歌词艺术|陆正兰:谈歌词的性别性
正文
2017-11-25 21:00 来源: 符号与传媒
谈歌词的性别性
陆正兰
以文本性别身份作为歌曲类别划分依据,流行歌曲可分为:男歌、女歌、男女间歌、跨性别歌及无性别歌。
1. 男歌
男歌是指歌曲文本性别身份为男性的歌,也就是说,这些歌适合男性演唱,通常也设计由男性歌手唱出,并意图让男性歌众传唱的歌曲。按歌曲中的性别标记和文化标记,男歌可以分为显形男歌和隐形男歌。
显形男歌
显形男歌即从歌曲的歌题上就能明显地判别出的男性文本身份歌曲。这些歌曲多为专门鼓励培养男性的精神和品格的励志歌。例如这首黄霑作词作曲的《男儿当自强》(林子祥原唱),歌文本中,就是用“我是男儿”来呼唤男性歌众,男儿要有傲气、胆量、理想、能量、热血心肠。
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第一首学堂乐歌《体操歌》也叫《男儿第一志气高》,由沈心工作于1902年,就是一首励志男儿的歌。“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做兵队操。兵官拿着指挥刀,小兵放枪炮。龙旗一面飘飘,铜鼓咚咚咚咚敲。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到身体好。将来打仗立功劳,男儿志气高。”
人类社会的发展,使男性成为“非标出的正常项”,但性别文化传统的作用力依然强大,男性的成长过程也会不知不觉地去迎合这种传统对男性的期待,这在歌曲中表现的很明显。比如郑智化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水手》,唱的就是这样一种感受:

年少的我喜欢一个人在海边,
卷起裤管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
总是幻想海洋的尽头有另一个世界,
总是以为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
总是一副弱不禁风孬种的样子,
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见水手说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显形的男歌情歌,从歌题文字上就可以判断,像《老婆老婆我爱你》(火风作词作曲,并原唱)、《你把我的女人带走》(温兆伦/王学真作词,温兆伦作曲,温兆伦演唱),《我爱的女人变了心》(郑东/郑源作词,郑源作曲,郑源原唱),《为我的女人唱首歌》(钟云飞作词作曲,并原唱),这些歌曲中明显的是男性对女性的抒说。
隐形男歌
大部分可以判定为“男歌”的歌曲,文本性别身份很少能从歌曲文字中描写自我的外貌特征上识别出来,相反会借言说中人物的性别气质,反推出言说主体的男性性别。这种男歌属于隐形男歌。比如这首陈涛作词,张宏光作曲的《你》(屠洪纲原唱):
你从天而降的你
落在我的马背上
如玉的模样清水般的目光
一丝浅笑让我心发烫
我没有那种力量
想忘也总不能忘
只等到漆黑夜晚
梦一回那曾经心爱的姑娘
歌曲中明显的性别指称要到结束时,“梦一回那曾经心爱的姑娘” 才点明,但在歌曲的一开始被言说主体“你”,用的是“如玉的模样清水般的目光”来描述,明显的女性特征词句,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言说对象的女性身份,这样言说主体“我”的性别也就很对应而出,这首歌曲的文本性别身份也随之确定。
2. 女歌
女歌是指歌文本性别身份是女性,适合女性演唱,经常也的确设计成由女性歌手唱出,并意图让女性歌众传唱的歌曲。
女歌同样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文本性别身份显形,二类是文本性别身份隐形。显形女歌,通常是指歌曲中有明显的女性性别指代,名词称呼,而且措辞风格具有女性气质,要求由女性演唱的歌曲;隐形女歌,通常指歌曲中没有明显的女性性别指代称呼,但内容上风格上具有女性气质,适合女性演唱的歌曲。
显性女歌
显性女歌,往往从标题上就能分辨出它是一首女歌。例如,《我不是坏女孩》(高以爱原唱),《我不是随便的花朵》(姜昕作词,虞洋作曲,姜昕原唱),《我不是你最爱的女人》(胡力作词作曲,李慧珍原唱),《女人的情歌》(雷青/金放作词,郑添龙作曲),《下辈子做你的女人》(白尘作词,栗子作曲,龙梅子原唱)等等,这些歌通常在文本中有明显的性别标记。这首《女人的情歌》,从歌题到内容都适合女性歌唱,是典型的显性女歌:
由施人诚作词,玉城千春作曲的《后来》(刘若英原唱),虽然歌题上没有性别身份标记,但歌曲文辞中出现明确的“女性语汇”:

桅子花白花瓣
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
爱你你轻声说
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
那个永恒的夜晚
女歌手李敏作词王蓉作曲的歌曲《我不是黄蓉》(王蓉原唱),从另一个方面体现出女歌身份:
我不是黄蓉
我不会武功
我只要靖哥哥 完美的爱情
我不是黄蓉
我整天做梦
在夜里唱情歌 失恋也英雄
歌曲的内容是女性的择偶倾向,歌后面明显是女性的自我表白,“我没有香香公主的美丽,也没有建宁公主的权力,我希望找到老实的郭靖,对人诚恳,对事精明”。这类明显标有带有女性文本性别的标记的歌,强烈体现出女性自我身份确认的需要。
隐形女歌
隐形女歌的文本性别身份就要稍微复杂一些,它们呈现的往往是文化规约性别。如: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的《女人花》(梅艳芳),歌题和文化规约性,就决定了女歌性别身份。正如苏珊·鲍尔多指出,“不论喜欢与否,在当前的文化中,我们的活动是被编码为男性或女性的,而且在性属/权力关系的主导体系中将会以这种方式运作。” “花”喻“女人”,“采”与“摘”隐喻男性对女性的拥有,是自古就有的文化隐喻。
而张浅潜作词作曲并原唱的《另一种情感》,则是将歌曲与文化正统中的“男性气质”相对比,从反面标明女歌身份:

昨晚你怎么来到我的梦里面
相对无语陌生又安全
我想赋予你英雄的气概
可它会在哪儿为我真实的存在
歌曲似乎很中性,但一句“我想赋予你英雄的气概”,明显的加重了对抒情对象的男性指涉。
一首歌是由言说主体和言说对象相互参照而成。也就是说,在歌中“我”和“你”依傍而生。歌曲中的男女性别形象是靠言说主体“我”对“你”即他者的欲望诉求而呈现的,“我”的欲望诉求对象“他者”,会像一面镜子一样,反照出言说主体的自我形象。
而所谓他者,也就是对主体起定义和合法化作用的一切,他者是主体之所以成为主体的原因。没有他者,主体不可能存在,因为主体依靠他者才能构成;反过来,没有主体,他者也不成为其他者,他者是为主体而出现的一个能指集团。因此,二者是“对峙”与“互塑”关系。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列纳维斯、萨特等人,都对主体与他者的关系作过更深入的说明:自我是被“他者化”的自我(altered ego)。


主体与他者关系,也很容易让人想起黑格尔的“主奴关系”。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主人与奴隶看起来是主宰和被主宰关系,实际上两者互相依存——无奴即无主,主人主要依靠奴隶“承认”。这种关系很明显,主奴之间有一方为主导,奴隶不可能在任何意义上“拥有”主人,他们之间有命令和服从为基础的不平等关系,一主一副。对主体常识性的理解很相似:我主他辅。这些微妙的主体与他者的关系,也会体现在男歌和女歌不同的文本性别中。
3. 男女间歌
男女间歌,指男女对唱的歌曲。也就是在一首歌中,一部分是男歌,一部分是女歌。这种歌曲的形式,就已经实现了男女性别呼应。通常,一般的歌只是或显或隐地用一种性别身份去召唤另一种性别,应答的性别人格是隐藏在歌之后的对话者,是歌曲潜在的意义延伸及实践。而男女间歌,呼与应不仅是立即有应,而且是现场反呼,互应互答。
男女间歌,常常预设了性别角色。比如这首一直流传的《敖包相会》(玛拉沁夫作词,通福作曲,李世荣原唱):

(男)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哪
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
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呀
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哟嗬
(女) 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呀
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
只要哥哥你耐心地等待哟
你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哟嗬
“月亮”旁边必须有“云彩”来相伴,这种带性别特征的比喻思维,自然让歌中的男主人公有了一个期待,同样,只有“雨水”浇灌,海棠花才会盛开,女性对男性的期待,自然也是一种带性别特征的等待。所以,对“哥哥”的要求是一种女性式的爱情考验。
另一首流传广泛的四川民歌《康定情歌》中,也有鲜明的性别角色约定:

(男)李家溜溜的大姐
人才溜溜的好哟
(女)张家溜溜的大哥
看上溜溜的她
(男) 一来溜溜的看上
人才溜溜的好哟
(女)二来溜溜的看上
会当溜溜的家哟
(合)月儿弯弯弯弯
会当溜溜的家哟
尽管歌中唱出了世界男女美好的乌托邦式的恋爱“世间溜溜的女子任你溜溜的爱哟,世间溜溜的男子任你溜溜的求哟”,但 “人才(相貌)好”,“会当家”,还是这类传统情歌中传递的选择妻子的重要标准。不只是民歌中有着鲜明的角度定位,当代情歌也暗含这种性别脚色定位。
男女间歌作为男女对唱的歌曲形式,在其表意过程中,歌曲的“性别性”会不自觉的迎合歌曲性别的演唱“角色”,从而加重性别文化程式中的性别角色意识。
男女间歌中的性别呼应
由丁晓雯作词,梁济文/梁雁翎演唱的《慢慢地陪着你走》,有一种对话式的呼应,情感在两个人中慢慢展开:

(男) 轻轻地牵我的手
眼里有满满的温柔
(女) 暖暖的感觉
默默地交流
不要太快许下承诺
(男) 慢慢地陪着你走
(合) 慢慢地知道结果
同时,男歌和女歌中性别意识也慢慢出现。男歌中“爱的话不要着急说出来”,暗示了男性在爱情关系中,通常是最会轻易表达,最会许下诺言的,而女歌中“不要太快许下承诺”,同样也暗示了,在爱情关系中,女性应该多等待,不要积极主动。尤其在最后,是女性的请求“每一天爱我更多 直到天长地久”,这是女性的期盼,同时也是性别关系中,男性最不容易做到的。一首男女间歌,写出了不同的性别表达和期待。
与其它文本性别身份歌曲不同的是,男女间歌多了一种舞台“表演”性。歌文本在两种不同的性别声音呼应中展开,歌众更像是一个外在的观看者、倾听者,通过一种观摩而得到一次情感认知。
4. 跨性别歌与无性别歌
跨性别歌是指叙述主体与叙述对象有清楚的性别间对应,但在歌唱实践中可以混用:既可以让男性向女性传唱,也可以让女性向男性歌众传唱的歌曲。一般来说,它应该提供给男女歌众都有的文化思想,社会态度及情感方向。
当代词作家方文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概念情感公约数:“歌曲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取得情感的最大公约数,也就是大多数人会遇到的感情状况,它最常成为歌曲的内容。歌曲一旦传唱就是针对所有的人,创作的题材和内容就一定要符合大多数人的情感现状。”这样的一种歌曲理想,实际上就要求更多的“跨性别的歌”出现。
的确从文本性别身份上,跨性别歌不像男歌和女歌,有着显形或隐形的“性别标志”,跨性别的歌很难从歌题和内容上识别,但必须在两性情感关系中展开。比如这首《爱你在口心难开》(依风作词,Pual Anka作曲,凤飞飞原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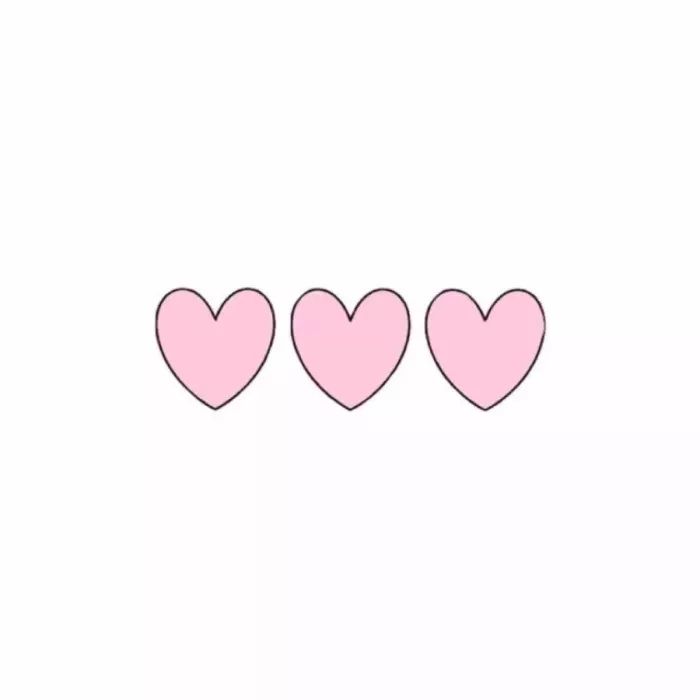
爱你在心口难开
你可知道我在爱你
怎么对我不理睬
请你静静告诉我
不要叫我多疑猜
喔喔耶耶
爱你在心口难开
这种因为两性之间的误会造成的若即若离的情感体验,男性和女性的情感经验中都可能有所共鸣。演唱它,可以不顾及各自的性别身份要求。
应该说,跨性别的歌占流行歌曲的主要部分。因为,歌必意图流行的性质决定了跨性别歌的占有歌众率。跨性别的歌可以同时在男女歌众中传播流传,这是流行歌曲的体裁要求。同时,流行歌曲,尤其是情歌更是男女情感交流的一种表意方式。性别差异造成的两性沟通,一直是歌曲中的很重要主题。
两性之间如何获得一种比较有效的沟通,这是心理学要解决的问题。歌曲作为一种艺术文本,也是透析并两性敞开自己的一种情感释放手段,不难看出,上面举出的这首歌,两性之间不知如何“相互取悦”的烦恼,是这首歌的基本“母题”。

事实上,男女之间的心理既有差异,也有很多相同之处。正如荣格的人格分析理论学提出的,在男性身体里存在女性的气质,他称阿尼玛(Anima);而女性身体里也存在男性的气质,他称阿尼姆斯(Animus)。阿尼玛和阿尼姆斯的存在,是两性相互理解的基础。因为只有两性间存在相同之处,才有进一步相互理解个性的基础和可能性。
张雨青提出,“从人格分析理论讲,两性之间沟通的一个有力的办法就是唤醒异性身体里的阿尼玛或者阿尼姆斯。阿尼玛或阿尼姆斯在人体中的含量因人而异,即使同一个人的阿尼玛或者阿尼姆斯含量在不同时期也会不同。因此,对于男性来说,改变身体中的阿尼玛含量能够改善他与女性的关系。同理,女性也是如此。”
跨性别的歌文本,意义在于在两性沟通这方面,能唤醒异性身上的阿尼玛或阿尼姆斯,尤其对于男性来说,歌曲更能是展现人格中阿尼玛的阴性品质的绝佳途径。叶嘉莹在《中国词学的现代观》里的观察相当犀利:“小词本是配合隋唐之间一种新兴音乐来演唱的流行歌曲,并没有什么深意,然而当它落到诗人文士的手里之后,在他们的潜意识之中不知不觉地达成了这种微妙的结合形成了一种双性的人格和双性的品质。”


所以,跨性别歌曲文本是展示一个人身上的阿尼玛或阿尼姆斯两种属性,以便提供两性沟通的一种方式。两个个体不可能达到完全理解,但我们可以作无限的努力。“我们应使自己习惯于这种想法:男人具有阳刚之气,女人具有阴柔之美,可每一性都兼有另一性。”两性交往中,需要持有正确的思想观念,要有同等人的观念,不要刻板地理解异性,不要把异性当做是不同类的人,应该以一颗开放的心灵去体验别人的生命。
正如英国作家伍尔夫指出的:“我们每个人,都受两种力量制约,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在男性的头脑中,男人支配女人,在女性的头脑中,女人支配男人。正常和适意的存在状态是,两人情意相投,和睦地生活在一起。
如果你是男人,头脑中女性一面应当发挥作用;而如果你是女性,也应与头脑中男性的一面交流。”跨性别歌唱出的其实也是一种两性情感的共同心理基础。对女性来说,“只有在我们身上的女性特质觉醒并且进入生命之后,我们才能找到出路走出共生。”
正如这首《解脱》(姚若龙作词,许华强作曲,张惠妹原唱)所唱:

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
我不应该还不放手
你有自由走
我有自由好好过解脱
是懂擦干泪看以后
找个新方向往前走
这世界辽阔
我总会实现一个
这样一首跨性别歌,当由女性唱出来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女性独立、坚强,阿尼姆斯的一面。
在性别关系上,对既男又女(androgyny)的生理身份,社会容忍度很低,实际上,这是文化对人格中阿玛尼和阿尼姆斯的强行偏执,但在歌曲文本中,各类广告中,各类衣装中,甚至各种社会角色中,却无法避免。人的生理属性,把他们的性别身份强行决定了,而文本身份却更依靠社会文化,因此更加多变。
5. 无性别歌
无性别歌表面上看不出性别,或无特殊的性别色彩,也就是可以供任何性别的人歌唱。这一类歌看起来简单,却很复杂。很容易和跨性别歌混淆,因为歌中也会出现“你”、“我”这样的人称代词,比如这首陈佳明作词作曲的《阳光总在风雨后》(许美静原唱):

阳光总在风雨后
乌云上有晴空
珍惜所有的感动
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
阳光总在风雨后
请相信有彩虹
风风雨雨都接受
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
然而,这类无性别的励志歌曲,往往在“你”“我”之间没有性别区分。这是和跨性别歌最重要的区别。歌曲旨在建构一种理想和信念,歌曲上体现出一种积极的性别平等的追求。
在所有的歌曲中,无性别歌曲中“我”和“你”在歌中的指称性最弱,实际上背后隐现的是一个共同的“我们”这样一个主体。最典型的无性别歌文本是直接以“我们”作为叙述主体的,通常此类歌的发出主体与接受主体,具有“全民性”,既然以全体人民为表意对象,文本就不应该有性别性。比如,罗大佑作词作曲的《明天会更好》:

唱出你的热情
伸出你的双手
让我拥抱着你的梦
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让我们的笑容
充满着青春的骄傲
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即使是前文举例由男女歌手刘欢和韦唯一起演唱的《我们亚洲》(第十届北京亚运会主题歌),两种不同的性别声音,但发出的主体以及受召唤的主体也都是无性别的,是“我们性”的。与性别间歌不同的是,不同的性别声音之间不是一种对话关系,而是一种共性的关系。在这种共性的关系中,并没有性别意识, “你”和“我”和在一起形成“我们性”意义。
歌曲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它也有其特殊的文化功能,对歌从文本性别上分类,并不影响歌曲文化功能的认识。一首歌可以有多个服务的目的:教育目的、鼓动目的、纪律仪式目的、审美目的、娱乐目的等。但一首歌之所以区别于另一首歌,更在于一首歌中主导地位的目的,而主导目的决定了一首歌的门类。这个原则与其他文学艺术、体裁的分类标准是一致的,现代文化理论家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等人早就详细阐述了主导因素决定门类体式这个原理。在无性别歌中,我们明显地感觉到,歌的目的性更多地在于召唤一种集体意识,激发人性一种积极向上共同的情感,一种人类的深切关怀,这种歌曲很多。
无性别的歌的“我们性”,是超越性别意义的一种情感和志向。它存在于很多题材的歌曲中,可以激发人类除了男女爱情之外的歌中情感,比如,爱国之情,朋友之情,励志之歌等。
“我们性”呼唤的是人类面对某种心理事件时的共同情感。这种情感往往是与性别意识无关的社会或某个群体的人文关怀。
本文刊载于《歌词艺术十二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年版,有增删
图片均来自网络
责任编辑:武学颖
摘要与附加信息
这篇文章由陆正兰所著,讨论了歌词中的性别性别一主题,通过对流行歌曲的分析,将其分为男歌、女歌、男女间歌、跨性别歌和无性别歌等多种类型。文章详细探讨了每种类型歌词的特征,并结合具体歌曲示例,阐述了歌词在性别身份表达中的重要性。文中指出,歌词不仅能够反映出社会对性别的期望和角色安排,也能在“跨性别歌”和“无性别歌”中体现出更广泛的情感共鸣和社会观念。特别地,陆正兰强调了跨性别歌曲在沟通两性心理和情感上的作用,认为这种歌曲可以唤醒男女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以实现更深层次的情感交流。整篇文章深入探讨了性别、文化与歌曲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摘要与附加信息为自动生成,仅供检索与参考。如有错误或遗漏(未知),请协助编辑指正,不胜感激。
附加信息 [Processed Page Metadata]
| Attribute | Value |
|---|---|
| Filename | www_歌词艺术|陆正兰:谈歌词的性别性_-_搜狐.md |
| Size | 21906 bytes |
| Archived Date | 2024-11-07 11:38:31 |
| Original Link | https://www.sohu.com/a/206663766_258583 |
| Author | 陆正兰 |
| Region | 中国大陆 |
| Date | 2017-11-25 |
| Tags | 跨性别, 歌词, 性别研究, 社会文化, 流行歌曲, 情感交流, 性别角色 |
| Evaluation | [Unknown type(update needed)] |
本文由跨性别中文数字档案馆归档整理,仅供浏览。版权归原作者所有。